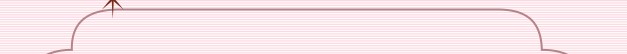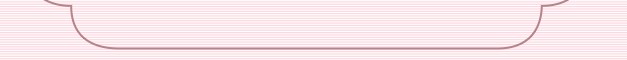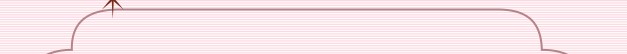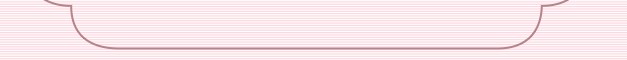|
|
|
|
|
|
音乐与孤独之遐想
|
| |
|
";}?>
|
每当我听着贝多芬、舒伯特、肖邦、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深深被他们伟大而悲怆的心灵所震撼,此中我听出一种摇颤心旌的孤独。
人常说:音乐可以解闷。依此,音乐也就可以解除孤独了。然而,孤独不是闷,真正的孤独也无从解。
所谓闷,大约是生活流程的一种阻滞,一种周期性的心理郁结,一种不畅不顺之感。这时,换换生活环境,改改生活习性,变变生活位置,也许这种闷会消除掉。而孤独呢,乃是人的生命的本质情结,任凭对生活涂抹什么样的色彩,孤独的原色总是不变的。人在独处之时正立足着孤独的本位;而人在群体之中则会印证孤独,维护孤独。前者说明自身对孤独的无力,后者说明外物对孤独的无助。总之,孤独无以解,无从解,与身俱来,与心俱在,就算人们自身创造的最有瓦解力的文学艺术对于孤独也是无可奈何的了。
可是,孤独却离不开音乐,真正的孤独者每时每刻都在寻找音乐,在生命中等待音乐,在音乐中等待生命。
音乐是意志,是世界得以构成,人类得以生存的意志本身。叔本华如是说。
音乐就这么无可抗拒地走进了人的生命,融化了人的生存意志,也就融合了孤独。唯有孤独者理解它。
当尼采将他的查拉图斯特拉从幽栖了三十年的深山拽出来,面对头顶上这个崭新的太阳时,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现呵!这是强有力的音乐对孤独生命的贯注,是两者的天然契合。理查德·施特劳斯用他的音诗实现尼采的精神创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头的动力音型不正是生命的贯注吗?中段的赋格流水般的潜动不正是音流对孤独的契合吗?
试用最清纯的头脑去想象瓦格纳带给我们的《帕西法尔》吧,一个地地道道的原人,一个只用音乐来表述的心灵。瓦格纳用这种心灵构建了音乐人生,用它解救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孤独者由此领悟了自身生命的底蕴。
勋伯格选择了孤独者最是心灵澄澈的时刻——一个月明星稀的子夜,一片树林之中,两个朦胧的影子:她说她已有身孕,但不是他的,他默然地爱着她。渐高渐低的音流细述着这种无声之境,梦幻般的弦乐如此地惊心动魂。我们内心永远铭刻着这个“升华之夜”。
孤独者对音乐的感受是独特的。不象一般寻求快乐、寻求解闷的人那样,用愉悦的心情去接受音乐。孤独者是在生活困境、心理无所适从的状态中,浑觉无聊、漫不经心地猛然与音乐相遇产生无可名状的颤动、怅惘、激愤、痛苦……。他注意到了笼罩在周围的乐声,但没有庄子“空谷足音”的快感,也不似萨蒂“身边音乐”那么轻易随风飘逝,可能是在这二者之间。
巴赫的管风琴,亨德尔的赞美诗,自天而降,不绝于耳。——孤独在颤动。
贝多芬的英雄呼唤,李斯特的浮士德意志,卷土而来,电闪雷鸣。——孤独在激愤。
勋伯格的难以追踪的变奏,韦伯恩的短小的生命动机,不平而鸣,欹重欹轻。——孤独在痛苦。
肖邦的忧郁夜曲,德彪西的闪动意象,沁脾而入,光色不定。——孤独在怅惘。
孤独者正沉重地体验着音乐的生命。与其说他在体认音乐,毋如说他借音乐体认自身,体认孤独。他既在音乐中自陷,又在音乐中超拔,一切都在音响中泫洗,一切又会到了没有音乐的过去。
应该说,不是音乐符合了孤独,而是孤独创造了音乐,孤独本身就是音乐,它与它都是一种生存意志。
贝多芬曾说:“我的日子过得很孤独!孤独!孤独!”是呵,不是孤独就不是贝多芬,从而也就没有贝多芬音乐。
孤独的生存意志铸成了音乐大师奇特的独身,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等等大师不仅令人品赏音乐中的爱,而且令人品味他们那种孤独对爱的超越。
也许该说,伟大的音乐正是孤独的人生,而孤独的人生正是伟大的音乐。 |
|
|
| |
|
|
|
|
|
|
 |